孙远钊:从著作权独创性谈中超联赛直播案 知产法网编者按......
时间:2018-04-16 出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知产法网)原载知产库 作者:孙远钊
孙远钊:从著作权独创性谈中超联赛直播案
原创 2018-04-04 孙远钊教授
知产法网编者按:
本网经作者授权特登载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孙远钊教授所著《从著作权独创性中超联赛直播案》一文,该文从国际公约与版权法发达的几个国家比较法的视角,结合我国近期法院审判的有关体育赛事、网游直播的热点案件,细致分析介绍了国际处理这类纠纷的情况和发展趋势,刨析了相关国际公约以及主要国家适用这些国际公约、各国法律的情况,并结合我国著作权法修改稿就立法和司法的应对,提出颇有建设性意义的独到见解。最为可贵的,本文又将实务问题回溯到著作权法领域作品独创性等基础理论问题上,精心分析论理、严谨推论论据丰富,并娓娓道来,是本专业研习、借鉴不可多得的力作。建议一读。
近年来在版权、商标权等领域,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引得探讨争议不断;法官、律师办案适用法律引用法条也困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赛事、网游直播就是其一;网络传播行为中所谓“非交互性”传播明确构成侵权而援引法条仍不得不引“弹性条款”;商标法领域的商标使用行为的含义,突破物理粘附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标识不算商标法上使用的“定牌加工”问题,争议从前次商标法修法前后若干年,法院对这类案件适用法律及认定理由也各有不同。原因归结起来,突出的是有的法律规范规定得欠清楚欠明确,缺乏及时的立法解释;还有的是某些规范整合立法时就存在疏漏。明确的法律规范、及时的立法解释和公正的司法裁判,恐怕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特色,其可以出高效率、出大生产力,当社会和市场发展需求及新鲜经验须总结时,尤其是这样。
壹、引言
2017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年会上,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六位学者和律师对于体育赛事与电子游戏的实况转播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论辩”(主办方特别强调不是“辩论”,因为不打算从事如同学校里那种故意针锋相对、立场极端分明的争辩)。
但还是再次引发了“著作权究竟在保护什么”的争论(也正是整个著作权保护体系当中的“大哉问”[1]),尤其是究竟要如何定义何谓“独(原)创性”以及是否需要达到如何的“创作高度”才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依据《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所要保护的客体是“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进一步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究竟何谓“独创性”?其中是否应有如何更为具体的标准?现行规制以及还在审议中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简称《送审稿》)都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规定。[2]本文试图从国际公约与比较法的角度来探讨此一根本性的问题,并由此检视体育赛事本身和对其直播的著作权保护等相关问题。
贰、国际公约的规范与启示
从全球立法政策的视角来看,1886年制定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简称《伯尔尼公约》)依然是当前国际著作权保护最重要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一。即便在世界贸易组织辖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Protection,简称《TRIPs协定》)之中,第九条更明文规定,包括著作权的构成要件与定义等都必须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例外是关于人格(身)权的部分)。
一、国际公约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对于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给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规定:
“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文字作品;讲课、演讲、讲道和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舞蹈艺术作品和哑剧;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和版画作品;摄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实用艺术作品;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插图、地图、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品。”
《伯尔尼公约》同条进一步规定,对于各类文艺作品的翻译、改编、乐曲改编以及其他变动等衍生性的作品应得到与原作同等的保护,并且不得损害原作品的著作权。《TRIPs协定》第十条更进一步把计算机软件程序以及数据与其他材料的编辑等都纳入了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畴。
从《伯尔尼公约》第二条规定所使用的开放式文句可以看到,公约对于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围只设定了所谓的“地板”(floor,意指最低标准或保护底线)而非“天花板”(ceiling,意指保护上限)。各个成员国自然可以依其主权,透过本身的国内立法对更多的作品类型提供更多的保护。这就意味著国际公约对于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采取了低门槛标准而不是高门槛。[3]
必需指出,由于《伯尔尼公约》在第一条便开宗明义的指出是“为保护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而制定,通说认为这就已经明确了著作权的保护制度是为了保护自然人(作者)的创意作品而设。[4]
此外,依照十九世纪的一般英语用法,“science”应当译为“知识”(knowledge)而非“科学”方才更为精准,因为有证据显示这应该正是《伯尔尼公约》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这个字时的“心中所想”,是在1886年公约制定时直接借鉴了当时既有的一些双边国际条约的文句而来,其中对这个文字的用法就有进一步的说明。[5]
二、可受保护的标准
虽然《伯尔尼公约》并未明确规定,但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在判定是否要给予著作权的保护时所一致要探究的根本性或关键问题是:一个作品是否显然由其作者自身的智力创作所产生,而不是从某个或某些其他既有的作品复制而成?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传统上是以“独(原)创性”(originality或originalauthorship)来表述特定的作品是源自作者的创意而非抄袭或复制他人的既有作品。[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9世纪的一个经典判例中已经表明:“只要不是抄袭自其它的作品,一本书的著作权即为有效,无需顾虑其中的主题是否具有或需要具备新颖性。”[7]
虽然如此,在司法实践上一些法院曾经适用具有相当创作高度要求的所谓“额头流汗”或“勤勉”法则(sweat of the brow,也称为“勤劳汇集”industrious collection)来作为检测是否具有“独(原)创性”的标准,但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最大的争议之一是,既然凡是透过一定智力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就当然享有权利,那么就产生了当事人何以竟然对特定的“事实”(如一个数据库内的数据的本身)也能享有著作权的荒谬现象。[8]
这个情况一直要到1991年才获得厘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白页电话号码簿著作侵权》案(简称Feist案)首次对于究竟何谓“独创性”给出了定义和诠释,而这个见解也对后来全球著作权保护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9]
法院明确扬弃了“额头流汗”法则,并表示:“虽然独(原)创性传统上是指特定的作品必需是作者所独力自为的创作(相对于复制他人的作品),……该作品还需同时具有某种最低程度的创意。”法院进一步表明:“所要具备的创意程度极低;即便只是稍许的含量仍已足够。”[10]除了解决“额头流汗”所造成的问题外,法院采取低度创意的观点也正是符合了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以著作权的开放授权来作为激励创意和促进文化传承的基本政策。
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或法院基本上也在探求一个作品是否具有作者的个性或人格性(personality)。例如,德国《著作权暨相关权利法》(Gesetz über Urheberrecht undverwandte Schutzrechte (Urheberrechtsgesetz), UrhG)第二条第二款便明文要求只要能构成“个人智力(慧)创作”的作品(Werke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sind nurpersnliche geistige Schpfungen)便可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又如意大利《著作权法》第一条第一款也要求必需是“作者具有创意特征的智力创作”(creazione intellettuale dell’autore)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11]这都与《伯尔尼公约》所采取的开放式授权与低度创意门槛的要求相互一致。
必需特别强调,大陆法系立法对于作者智力贡献的要求不可被曲解或误认为是对于一个作品可否受到保护所必需达到特定的“创作高度”(Schpfungshhe, heightof creation)。
例如,德国著作权法对于文艺作品的门槛要求是只要有“轻度改变”(kleine Münze, small changes)便可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并判决其中包括了操作指令、为司法判决所准备的注释笔记等。[12]德国法只是对“设计”才要求必需具有更高的“创作高度”以便受到保护。又如荷兰法对于极为平常甚至瑣細的撰述(even the mostbanal or trivial writings)等都赋予著作权保护。[13]
在法国,其著作权法(或作者权法Le droit d'auteur,并无独立的单行法,而是规制于《知识产权法典》第一卷)第L111-1条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仅仅基于其创作的事实,就该作品享有排他及可对抗一切他人的无形财产权。”[14]因此只要是属于各自的独立创作,依照法国法就可能有两个内容完全一致的表达都可分别获得各自的著作权保护,互不侵犯。[15]
至于日本《著作权法》则规定,“著作物”(作品)是指“用创作来表现思想或情感并属于文艺、学术、美术或音乐领域的原作。”[16]
欧洲联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简称欧盟法院)在2012年的《足球联盟赛程表》案判决确立了欧盟对于“独(原)创性”的标准,与美国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17]法院表示,作为能获得著作权保护的要件,“智力创作”是构成“独(原)创性”的唯一要求。因此当作者依其自由和创意的选择以原创方式来表达其创作能力时,就已具有“独(原)创性”。
反之,如果对于诸如数据的安排等是依据技术考量、规则或限制所做成,其中并无如何的自由创作空间时,其结果便没有“独(原)创性”可言。法院并确切指出,在数据库的情形,涉及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对于该数据库的“结构”,亦即透过如何的“选择”与“安排”所形成的框架组织,而非其中的“内容”,也就是完全不及于数据的本身。
由此可见,固然采取不同法系的国家在表面上所使用的文句或许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因为承认人格(身)权,所以著重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个性”);英美(普通)法系则是著眼于特定作品与先前其他作品的比较(作品的“创造性”),但详细检视便不难发现这两者无非是一体的两面,必需相互为用。否则如果没有作者自身的“个性”,又何来“创造性”之有?反之亦然。[18]
换句话说,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两大法系的论述并无如何实质上的不同,法院根本不会也不应去探究特定作品的美学价值、创作目的或是社会反应,而是单纯、直接地去检视作者对作品确是独力自为并有创作(或贡献)即可,完全无须顾及最终的结果或目的为何,更与其创作是否产生了如何的正面或负面价值等完全无关。[19]
三、著作权在分析(比对)什么
俗话有云:“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不是在说天下所有的作品都必然是抄袭之作,而是在体现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创作都是牛顿所说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在一定的程度上无可避免的需要借鉴先前既有的材料然后再依作者的构思、创作从事某种转化而生。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每天都必需仰赖外来的食物,消化吸收后再转化为自身所需的养分。
如果真有文学或艺术作品是100%完全独创(就彷佛两个婴儿使用成年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话语”彼此牙牙对话),或者在规制上做此要求,其结果就只能认可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才享有权利,但却同时注定了那恐怕只会曲高和寡、乏人问津,因为根本无人能懂得或是体会其中的意义,同时也因为能获得著作权保护的门槛订得太高,反而会让著作权的保护制度根本无法达成激励创新的基本宗旨。[20]
既然任何作品都必需借鉴之前既有的其他作品(或经验、体会),就如同所有的人原则上都得有四肢五官和各种必要的生理系统。如果就直接从事比对而没有先把不应被纳入的因素给事先去除的话(也就是诸如唯一、有限表达或是共同场景),自然就注定了人人都构成了对他人的“实质近似”和“侵权”,纵使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
这正是为何要透过“独(原)创性”的要求在制度上求取一个相对适当的平衡:作者所汲取的来源或素材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特定的作品是否经过某种转化再由作者自行表达或呈现,从而不是复制品或抄袭之作。如果借用欧盟的语境和表述,此种可受著作权保护的转化是指作者透过自行的筛选与安排(selectionand arrangement)来呈现对其作品的表达方式;如果借用美国的语境和表述,就是指作品的表达方式或呈现至少包含了一些最起码的个别创意。
也就是说,著作权的获得与侵权与否就彷佛在比对个别的一张张面孔或表象(表达方式);表面上人人都有相类似的五官结构,但却可呈现出各种不尽相同的相貌(有些个别特征)。有的相貌之间或可具有相当高的近似度,但只要是独自创作,就可分别享有自己的权利,互不侵权。
就如同在某个景点(如黄山的迎客松),前后两位身高、体型都相近的游客可以先后站在同一个位置,面向同一个角度,选的是同一个景致,用的是同一型的相机,使用同样的设定,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先后拍摄出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两张相片,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可能相差了几秒钟。其结果是两个人还是当然可以分别获得对其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并且两个权利同时并存,谁也没有侵害谁的权利。这也正可显现出著作权固然是力道很强的排他权利(exclusive right),但在先天上却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做为制衡:表面上的感知近似从来就不能做为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唯一标准。
归根结底,“独(原)创性”所指的就是并非抄袭之作,而是透过外来的影响、借鉴等在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再以自己的方式所转化出来的表达或呈现。不过这个貌似相当平铺直叙的表述却至少在实践上产生了三大难点或悖论,衍生出许多原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一)悖论之一:“创作高度”要求
除了“独(原)创性”的要件,美国的司法实践曾经一度更要求图像作品必需具有某种美学价值才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21]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03年一宗涉及马戏团海报的案件已经正式废弃了对创作高度门槛的要求。[22]法院已然认识到,让一些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士来担任对特定美术或图像、摄影作品等具有如何美学价值的最终审定者“是个危险的做法”,而且一些极具天分的创作势必无法受到青睐,恐会遭到误判。[23]后来的立法政策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只在涉及实用艺术或工业设计作品时才例外的会做此要求。[24]
英国传统上对“独(原)创性”是指透过作者自身技能、劳动、判断与努力(skill, labour, judgment and efforts)的投入所构成的独力创作,简称“技能与劳动”法则(skill and labour test),与“额头流汗”的概念相仿。[25]然而随著欧盟法院从2009年在Infopaq案[26]到2012年在《足球联盟赛程表》案所岀台的一系列判决,英国已面临极大的压力必需尽快修正此一法则。虽然英国经过2016年的公民投票已决定要脱离欧盟,其在经济、贸易上仍然无可避免的必需和欧洲共同体市场保持高度密切的联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必需持续依赖欧盟的法律框架与规制。这就意味著这个必需改变与整合的压力依然持续存在。
德国、荷兰与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也曾一度对于特定类型的作品(如计算机软件、目录索引、字典编辑等)要求必需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才可受到著作权的保障,但后来都已纷纷做出了改变。[27]到了欧盟法院2012年《足球联盟赛程表》案的判决岀台,除了对原本不具独创性的表现或表达(如数据库)要给予特别、例外性的保护时仍然要求必需具备一定的创作高度外,对于一般的著作权保护已经不再要求必需符合这样的高度要求或具有某种美学价值。
从立法政策上对于不同的作品要求必需具备不同的创作高度才能获得著作权,甚至据此给予程度不同的权利保护,不但与著作权的本质相悖,更注定会制造出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在实践上让当事人与法院根本无所适从。首先,各种类型的作品之间原本就是互有交集,并不相互排斥。什么样的作品需要达到如何的“创作高度”才符合可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原)创性”事实上是根本无法明确定义的。这就如同硬要在自己的手上画出一条线来区别手心与手背,固然在概念上两者貌似有所区分,但在实际上却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即使在同类型的作品,这样的要求也只会益加造成对整个著作权制度的不确定,让人无所适从。例如,同样是创作一首诗,从著作权保护的视角而言,某甲的灵光乍现、一挥而就与某乙的苦心推敲、三年方成,两者之间真有如何“创作高度”的不同从而应该受到不同程度的著作权保护?如果真有,其中的差异位在何处?由此也可再次显现“额头流汗”(智力劳动成果)理论与“创作高度”要求会引发出的荒谬结果。
(二)悖论之二:低度创意导致浮滥保护
反过来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只是设定对“独(原)创性”的一个低度创意要求,其结果将会导致许多原本不值得受到保护的作品都能轻易地取得著作权,淡化了创意的价值,让市场充斥著各种不计其数、被任意称为艺术的物件或表演,却反让真正的创作在寻求受众时更加艰钜。[28]
这个观点显然把著作权的本质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行销选择等给混为一谈了。无论是书籍(小说与非小说)、电影、电视节目、应用软件或是艺品画廊,其个别相关的市场早已形成了个别不同层次的受众与行销渠道,行之有年,就形同一个金字塔的不同层级一般。以小说为例,自然不是任何的作家或作品都能达到金字塔的顶端,赢得在书店最明显(也可能是具影响力)的橱窗予以公开展示的“荣幸”;以电影为例,也显然不因为某部影片被评论家认为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就当然表示会有票房或是应当取得最佳的放映时段。所谓“让凯撒的归凯撒”,这些事项本来就需要由作者们各凭本事去竞争,与著作权实在牵扯不上任何的关系。
(三)悖论之三:关键问题与举证责任的错置
参酌Feist案的见解,法院对于“独(原)创性”的要求只需审视两点:(一)作者自行筛选、安排与协调其作品的表达方式(“独”的要件,亦即不是复制其他既有的作品);以及(二)其作品展现出了某种最低程度的创造性(minimum level of creativity)(即“创”的要件)。据此,固然不是任何对资料的编辑都可当然过关,但只要能举证是以某种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呈现便已足够。[29]
由此可见,法院在处理关于“独(原)创性”的举证时,询问当事人的问题和审视的重点应当在究竟有沒有“独(原)创性”,从而确定是否具有著作权以及权利的归属即可,而不是要求当事人必需非常精确的指出其作品中的个别创意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法院应著重于确认作者对其作品整体的独创表达,而不是要求钜细靡遗的指出各个“独创点”位在何处。
反过来说,做为对于侵权指控的抗辩方式之一,被指控方才需要针对原告所具体指控的构成侵权部分反证那也是被告自身的独创表达,只是英雄所见略同,如同前述的两张表面相同的照片一般。被告亦可抗辩原告所指控的特定侵权部分原本就不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因为属于唯一、有限或共同场景或是属于纯粹功能性的表达等)或是原告对该部分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从其他来源所复制而得,并非原告的独(原)创。
这样的举证责任配置不但合乎立法政策的原始目的,也可避免诉讼经济与时间的浪费,否则会容易导致偏题,让双方从一开始便走上弯路,变成在作者(通常为原告)自己作品的有效性上头纠缠,而不是聚焦被指控的侵权物,让著作侵权诉讼原本已经相当困难的举证问题更成为雪上加霜。
在采取登记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否涉及对作品的实质审查,“在先登记”往往成为原告佐证对其作品具有原创的重要工具(至少在时间点上可做为创作在先的有利证明)。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作权法》更规定,凡是在作品首次出版之前或之后五年内获得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在任何司法程序中都会被视为已经构成了著作权有效的大体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30]
叁、体育赛事与电子游戏直播節目的“独(原)创性”
一项体育赛事的本身是否具有“独(原)创性”始终有相当的争议。[31]但是对于一场比赛从事直播应受到保护在国际间则是早有共识,并至少应适用1961年《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Rome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Broadcasting Organisations)甚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的相关规定。[32]
一、主要争议
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主要争辩大致聚焦在两处:一是现场直播画面的权利来源,也就是赛事的组织者究竟是否享有任何的权利、依据为何?二是对于体育赛事的直播应否给予任何的保护(尤其当权利来源不明确时)?如果答案仍为肯定,那么究竟应以著作权抑或邻接权(neighboring right,现已改称“相关权”other related rights,范围远小于著作权)来给予保护?[33]
关于第一点,赛事组织者是否享有如何的权利与经其许可从事现场实况直播所产生的著作权或邻接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更是两个独立的权属,一码归一码,各有所本,不可混为一谈。就如同一位武术师表演整套太极拳,虽然各种基本或制式动作原则上并无任何的独(原)创性可言,但他人的拍摄呈现则可产生独立的著作权。[34]又如整个阅兵的过程势必经过各有关方面的详细策划与现场协调、投入了不计其数人员的智力劳动所产出的成果,但该成果原则上也没有任何的著作权可言(没有任何特定的“作者”);但由央视与八一制片场分别对整个阅兵过程所拍摄的实况转播则享有各自的著作权或邻接权,互不侵犯。
由此可见,在赛事转播的情形,其组织者乃是提供了让特定广播制作单位或团队可以从事摄像的独家许可。虽然在学理上有时被称为“在地权”(house right),这个许可是基于球队(团)对特定场地的所有权(或专有使用权)再透过双方签订合同(合意)所产生,并不存在任何法律的特别授权或行政赋予。[35]
关于第二点,鉴于各种巨大的经济性与非经济性投入以及透过此种转(直)播所产生并支撑的重大商业利益,在立法政策上各国对于体育赛事的直播几乎都认为应给予适当有效的保护,而且一般均认为应透过著作权或邻接权的方式最为有效,真正的问题是发生在具体的细节上。
例如,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虽然规定了录像制作者对其制品享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但依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这项权利仅适用于“交互式”的网络传播,也就是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情形。这就导致录像制作者对未经其许可而从事的所有“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也称为“网络定时传播”)无法行使任何的控制或排除其未经许可的使用(或再转播行为)。
此外,《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了电视台播放录像制作者的作品应取得著作权人以及制片者或录像制作者的许可,完全没有涵盖到任何涉及到网站的直播或转播行为(更遑论直接撷取赛事直播的讯号然后在网络上从事“再转播”re-transmission)。然而目前涉及到对于节目直播的侵权行为主要就是第三方未经许可在其网站上透过“流媒体”(streaming)方式对原节目讯号所从事的再转播。目前的法律规制显然就偏在关键处出现了两个立法上的漏洞,让网站的定时传播或再转播几乎可以完全规避著作权的侵权责任。[36]
二、欧盟的实践与发展
欧盟法院的最近判决已明确表示,运动赛事的本身并不具有“独(原)创性”,因此无法获得著作权或邻接权。[37]由于邻接权的存在必需以对于曾经或仍有著作权的作品从事表演为前提,参与体育赛事的运动员从而也无法主张享有表演者权。[38]不过法院也指出,“体育赛事本身有其独特与原创的特质,或可转化为可受到与作品相类的保护。而此种保护可在适当的情况下由各国依其国内规制给予授权。”[39]美国的司法判决一向认为体育赛事的本身不足以构成具有“独(原)创性”的表达,因此也无法获得著作权。[40]不过当被告想假借新闻报道之名对原告的体育赛事行广播之实,从而达到免费搭便车的目的时,原告仍可以“热点新闻例外”(hot-news)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对利益的“窃取”(misappropriation)。[41]
虽然一项赛事的本身未必能够获得任何著作权或邻接权,但欧、美、日等地对于电视台或经许可对赛事从事拍摄、转(直)播的制作单位都给予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保护则没有如何的争议(虽然具体的内涵或有不同)。例如,欧盟鉴于影片的制作(包括体育赛事)往往涉及到相当大的资本投入与风险,而对其投资的可能回收必需依赖适当的法律保护,因此在《信息社会指令》(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简称InfoSocDirective)[42]和《出租指令》(Rental Directive)之中关于邻接权的部分还分别制定了一个特殊的“首次固定权”(right of first fixation),给予自首次合法发行(或是在尚未发行的情形,自首次固定)起五十年的保护期间,而且不以具有“独(原)创性”为前提(不过由于英国仅承认著作权,因此必需符合构成戏剧作品(dramatic work)的要件)。[43]
同理,广播组织对于向公众传播其讯号享有邻接权保护,其中包括排除他人对其体育赛事节目(包括直播)讯号以有线或无线等方式从事未经许可的固定、再转播与“向公众传播”(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等行为。[44]欧盟法院明确表示,在透过诸如互联网等技术方法从事再传播的情形(有别于原始的电视通讯),纵使原始的转播(或直播)已经被使用者收看或接收,并不影响也更不能免除透过网络向公众传播的第三方仍需个别向作者取得许可以从事对节目讯号或数据信息的再转播。[45]也就是说,纵使特定节目的内容欠缺受著作权保护的要件,涵盖该节目内容的讯号邻接权依然独立存在,完全不受影响。[46]
一个值得关注的最近发展是欧盟法院在2015年的判决以及瑞典最高法院随后的续判。[47]本案被告利用网络超链接(hyperlink)的方式让其使用者得以免费观赏由原告现场直播的冰上曲棍球(ice hokey)比赛。瑞典的上诉法院已经在先前的判决中认为原告并不具有著作权,但拥有对直播节目的邻接权(或相关权)。
等上诉到瑞典最高法院后,该院移请欧盟法院释疑的问题是:欧盟成员国是否可以对权利人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提供涵盖范围较《信息社会指令》第三条第二款更为广泛的保护?[48]在本案的情形,究竟对冰上曲棍球比赛的现场直播从事未经许可的链接(在技术上并非交互式传播,因此不构成“向公众提供”(makingavailable to the public))是否仍然可以构成“向公众传播”?此外,对于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是否符合著作权的保护要件?
欧盟法院首先表示,《信息社会指令》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本身并没有试图要求对于还未赋予其中所定权利的成员国要求整合的意思,毕竟欧盟各国的国内法在著作权和邻接权的领域迄今也只形成了部分的整合而已。虽然如此,《信息社会指令》同时承认并容纳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指令,其中的一个便是《出租指令》。根据后者,各成员国在广播和“向公众传播”方面可以提供给权利人远较该《指令》更为广泛的保护。此外,《出租指令》第八条也表明,各成员国必需给予广播组织许可或禁止(第三人)以无线方式对其广播从事再传播以及向公众传播的排他权,尤其该传播是做为公众原本必需支付费用的免费替代时。
欧盟法院最终认为,其成员国可以赋予广播组织在要件方面有别于《信息社会指令》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从事未经许可向公众从事传播的行为。而这也正是瑞典的实践。因此瑞典的国内立法并未违反欧盟的相关指令。[49]
案件在发回到瑞典最高法院后,该法院的续判只是聚焦在赛事的转播是否构成向公众传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之上,并未触及广播组织邻接权的问题。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三票)认为,本案的赛事转播已经构成了向公众的传播,但是依据瑞典《著作权法》,原告直播当中的评论、摄像、图片制作等,即使再加上一些周边的因素都还不足以达到具有足够独(原)创性的智力创作,包括在制作过程中所必需做的一些选择以及对一些图片设计的运用等因为那些因素等,都只是随著赛事的发展被牵引产生,因此广播组织对其直播节目并不享有著作权。但另外则有两位大法官对此持不同意见,显见法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相当的分歧。无论如何,纵使实况直播被认为构成向公众传播,但法院针对著作权的部分最终判决不构成侵权。[50]
做为对应,运动赛事的制作单位已在转播过程中尽可能的加上各种可能被视为具有独(原)创性的元素,希望能让其直播能达到受著作权保护的程度。[51]
三、美国的实践与发展
相对于欧盟成员国的分歧,美国国会在制定1976年《著作权法》时,便已经在立法理由表明:只要录像与讯号的传播是同时进行,现场直播就是属于视听(音像)作品(audiovisual works),应该完全受著作权的保护:
“当一场美式足球比赛是由四组摄像机来转播,并由一位导播来指导四位摄影师和选择其中何者所拍摄的的电子形象要以如何的方式向公众呈现时,摄影师与导播的作为几乎毫无疑问的已构成了“创作”(authorship)。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其中是否已经完成了固定(fixation)。如果要转播的形象和声音是先被录存(在录像带、影片等等之上)而后再予以转播,该录存的作品应被视为“电影作品”并受到法定排除未经许可的复制或再传播的保护。如果节目内容是以直播方式向公众传播而同时也一并录制,其案件将受到一样的对待;著作权利人在起诉直播的侵权使用者时将不会被迫诉诸于普通法而非法定权利。因此,假设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 例如作为“电影作品”或“录音作品” — 现场直播的内容……只要是随著讯号的传播同实在录制,应被视为已经固定并获得法定的保护。”[52]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之后进一步表明,一场球赛(在本案为职业棒球比赛)如果还未录像,那就意味著球员们的“表演”还未被固定,此时球员或许还有可能主张依据州法规定属于其个人的权利,然而只要比赛一被录像,就发生了依《著作权法》(联邦法)所定义的“固定”,形成了著作权,而球员原本或许享有的个别姓名、身份识别等权益(即“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与球赛中的“表演”也都因此而被完全融入了职业棒球大联盟所享有的著作权之中。[53]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在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判决中再次表示,体育赛事的本身无法获得著作权,但是对于赛事的转播则可。[54]这是因为从字面的常识性意义而言,一场体育赛事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作者”可言。固然对于一场赛事需要许多专业上的多方准备,但那些准备至多只是希望或信念的一种表达,想让特定事物发生的一种决心。这种先天上具有竞争性的活动因此与电影、话剧、电视节目、歌剧等以特定的剧本为基础所从事的表演完全不同。[55]目前既有的有限判例对于类似体育赛事或团体参与的电子游戏等组织性活动的本身几乎是一致的认为无法获得著作权。[56]
对于体育赛事现场直播以流媒体从事未经许可的再转播,基本上不外两种技术方案:所谓的“单播流媒体”(unicast streaming)方式,亦即由某个中央服务器特定对终端使用者从事“单点对单点”的信号传播,以及“对等网络流媒体”(streaming over peer-to-peer networks)方式,亦即不透过任何中央服务器,而是由互联网的不特定使用者相互利用彼此的装置资源同时成为对节目信号的传播分享者(“多点对多点”的信号传播)。“对等网络流媒体”在极短的时间当中便成了当前最为普遍的分享方式,其过程与网络的音乐、电影等分享非常近似,但其便利性与执法的困难也对侵权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57]
鉴于讯号的网络传播经常是跨境性质,美国的司法判决进一步表明,在“单播流媒体”的情形,只要有一部份的侵权行为是发生在美国境内,无论其最终的收讯或收播位在何处,也就是一旦未经许可所传播的讯号是源自美国境内,就可以适用美国的著作权与商标权法规。[58]至于在“对等网络流媒体”的情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指出,“凡是基于推广其侵害著作权的使用为目的而明白表示或采取其他积极的行为来推广其〔侵权〕装置的扩散,对于由此所导致的第三方侵权行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59]这里所指的是间接侵权,包括了帮助(或辅助)侵权责任(contributory liability)、代理侵权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与诱使责任(inducement)等三种可能的情形。[60]
在是否构成直接侵权的认定上,国会在通过1976年《著作权法》时,就是为了推翻法院过去区别“广播者”与“观赏者”的做法(以往的判决是认为只有“广播者”才会涉及表演权[61]),以三个法律条文确立了一点:只要是关于对节目画面与音效的传播就构成了对于节目内容的“表演”,从而把有线电视的各项讯号转播或再转播等行为都纳入到了著作权的范围之内。[62]
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件进一步判认,无论被告是否从事连续不断的节目讯号,或是透过如何的途径(包括网络、卫星等等)来传播或转播,实际上都已构成了“表演”行为。无论是“单点对单点”抑或“多点对多点”,应该直接从被告对讯号的传播所产生的客观或实际效应来研判是否其行为与有线电视的转播在本质上有无任何本质上的差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如何差异),那么就构成了“公开”。[63]
肆、问题分析
一、独创性的认定应趋向从宽
从上述的引介与分析可见,在当前国际整合与国际公约的整体框架下,作为保护和开展一个社会文化创意资产最重要的激励工具,并考虑到其本身在先天上的局限性,著作权的赋予是采取了尽量从宽而非从严的基本方针。欧、美等地对如何可以构成“独(原)创性”从而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思维与适用标准已是愈来愈接近。除了瑞典、英国等少数的国家仍然对“独(原)创性”采取“额头出汗”或“创作高度”的较高标准要求外,绝大多数的国家已经多少采取了类似美国的标准。
欧盟因为还未能完成对著作权实体法的全面性整合,在现实上便退而求其次,对于“独(原)创性”采取较高要求的成员国就只能认可以“邻接权”(或“相关权”)来给予保护,其所能涵盖的范围与期间自然较一般的著作权要相对限缩许多(不过欧盟则是规制了一个特殊的“首次固定权”)。而在美国,原则上只要符合作品是自行筛选、安排与协调以及最低程度的创造性等两个要件,而且不是诸如思想、程序、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理、发现等或纯粹功能性的运用或运作,就可以受到著作权(而非邻接权)的保护。
至于以往对于“创作高度”或“智力劳动成果”的要求,其实是一个悖论,毕竟那是个根本无从定义的抽象概念,如何能够区分“三年推敲”与“灵光乍现”之间何者的创作高度较高?[64]此外还会产生诸如对事实的本身亦可取得著作权保护的荒谬结果(欧盟已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不具“独(原)创性”的资料、数据汇编等便改以订立特别的指令(如保护数据库的指令)或单行特别法来达成,不再强行纳入到著作权的范畴之中,以免滋生问题)。然而这种没有客观标准的概念一旦成了认定是否具有“独(原)创性”的标准,就注定会成为整套著作权规制不能不套入的陷阱和误区,导致整个制度的混乱,反与著作权保护的宗旨背道而驰,让人无所适从,更遑论维系文艺传承、精神文明以及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科学事业的发展等所标榜的使命。[65]
二、邻接权的范围不应任意扩张
在另一方面,依然是在现行的国际公约框架下,“邻接权”(或“相关权”)是相对于作者对其文艺作品著作权之外的、范围相对也相当有限的独立排他权利。其所保护的客体并非作品的本身,而是对特定作品(例如电视节目或录音录像制品,无论该作品是否受到或仍受著作权保护)的表演(有别于著作权人的表演权,后者包括对节目讯号的传播等)、广播或首次录制(或发行)等三种类型,其所保护的主体则是表演者、制作人或广播组织,别无其他。[66]
换句话说,一旦不符合著作权保护的“独(原)创性”要件或要求,邻接权从来就不是、也更不应该成为退而求其次,做为帮衬兜底的某种事实上的“次著作权”。“独(原)创性”的认定固然有灰色地带,需要依照个别案情的具体事实来详细分析审定,然而一旦被认定,是否享有著作权就是黑白分明。与邻接权绝不可以混为一谈。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一般论述其实并不符合国际规范,恐怕需要尽快做出修正,以免形成误导。
三、赛事直播应有著作权
反应到对于体育或电子游戏赛事的直播与再转播,无论是欧盟抑或美国,目前透过司法实践都已经完全确认是可以受到保护。这与体育赛事的本身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保护并不需要有如何直接对应的关系。因此凡是对节目讯号从事未经许可的传播,原则上就构成了对该节目向公众从事信息网络传播(或公开传播)的侵权行为,个中的差异只是在究竟应该以著作权或邻接权的方式来给予保护,从而影响到的是权利人所能主张的排他权的具体内涵和范围。
按照目前的多数观点(通说),是把体育赛事直播归类为现行《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所规定的“类似设置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或称“类电影”作品)。这虽然有些勉强,但并非不能成立。一场体育赛事与传统的电影呈现毕竟有著一定的不同,除了少许的例外(如摔角比赛基本上都是事先策划好的表演),原则上并没有事先拟好的剧本,也没有各种预设的场景布局与事后的剪辑。不过目前也有许多的电视节目是采取了所谓的“真人秀”(真人实境realityshow)模式,其中的各种情况与体育赛事可说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除了一些必需依循的基本规则之外,也没有任何的剧本、不同场景布局、剪辑等,几乎要完全依靠临场的实际发展与变化来从事机动性的调配。
另一种观点是把体育或电子游戏赛事的直播视为《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九项所定、做为兜底之用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做为现行法保护空白(或不足)的无奈。[67]不过这就更为勉强了,因为目前在其他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当中确实还找不到任何可以把体育或游戏赛事直播节目直接归类为如何作品的规定。实际的状况是,体育或游戏赛事的直播就是一种“视听作品”(audiovisual work),只要影像与声音的录制与讯号的传播是同步进行或是“先录(固定)后传”,就应受著作权的保护。现行法在面对新型的问题时不免会显得捉襟见肘,而拟议中的著作权法《送审稿》已准备增列对于视听作品的定义和保护,应有效对应当前的困境。[68]
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纠结体育赛事或电子游戏的直播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作品”,而是迳行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即可。[69]不过其中的问题是,第四十五条在制定时显然只是关涉对于广播或电视节目的传统式播放,当整场赛事是透过互联网来直播时,是否依然可以把这一条规定扩张适用,仍然不无疑义。[70]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新浪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简称《中超体育赛事直播》案)的二审判决一方面也是支持直接以《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做为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完全否定了赛事直播可以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71][72]法院认为,涉案赛事整体比赛画面尚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不能满足电影作品中对于“固定”的要求。赛事信号所构成的载连续画面在素材方面基本上并无个性化选择,而在对素材的拍摄、对被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等方面的个性化选择空间则相当有限。因此,从类型化的角度而言,其独创性难以符合电影作品的要求,也就意味著根本不受著作权的保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见解显然与目前的国际趋势相反。法院采用了传统的类型化方式来推导,也就是先检测体育赛事的直播能否套进现行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作品类型,然后再据以决定是否受到著作权的保护。法院首先明确表示,司法在《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类型之外无权设定新的作品类型,因此也就完全排除了套用该条第九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可能,这是正确的。法院继而表示,“固定”于特定的载体是获得著作权的保护要件,这也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法院接下来以两个理由判决此种直播节目无法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就恐怕值得商榷了:
(1)以“随摄随播”的方式呈现连续画面的信号传输“未能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尤其是没有“摄制在一定介质上”,从而不符合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法院认为要到直播结束,信号所承载的画面整体已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才符合“固定”的要求);
(2)赛事的转播无论从素材的选择、拍摄与画面的选择编排都不具备足够的独创高度,因为其中不具足够的“个性化选择”。[73]
其实当法院采取了类型化的套用测试之际,也就是“先看可能是哪类作品,再看究竟有无著作权”恐怕就已经产生了本末倒置的问题,而对于相关的国际公约条款采取狭义解释恐怕也又与当初的制订原意刚好相左。
首先,凡是符合著作权产生的定义(也就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并且不在不受保护的例外之列的(如思想、程序、系统、概念、功能性的操作方法、唯一或有限表达、共同情境等),当然就应该获得著作权,至于究竟符合哪种作品类型则是下一步。除非法律对于特定的作品类型又有如何特别的规定,一个特定的独创表达有可能同时兼具两种或以上的作品性质,彼此之间并不当然相互排斥;反之,如果未必完全符合对于特定作品类型的描述或定义,也不会、更不能因此反而导致失去著作权的保护。
其次,《伯尔尼公约》(无论是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或1971年的巴黎会议文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在制订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商用性的互联网,其中许多的规定显然无法对应各种网络新型科技与商业模式所引发的行为或问题。虽然如此,公约的制订者显然早有认知,所以对于各类作品的定义采取了开放、包容与广义的原则。[74]即使按照二审判决的思路来推导,《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关于“类电影作品”的规定,其制订的原意是指“透过制作的程序呈现出类似电影视觉效果的作品,并透过某种有形物质的支撑被视为电影作品”。[75]也就是说,其重点在于对作品最终的视听效果呈现(独创表达)是否与电影类似,而不是制作的过程要与电影相似。[76]
第三,如果依然根据二审判决的逻辑和步骤来分析赛事直播是否具有或是符合“固定”的要件,参酌世界贸易组织的解释和说明,电影或作品的成立与否未必需要以“固定”于某种物理的介质为前提。[77]例如,即使是传统的电视节目转播,无论在同个新闻节目当中是播出一则经过事先以录像带预录的报道或是一则现场的实时报道,除非事先告知,对于观赏者的感知而言是几乎难以区别的。在网络环境下,流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各种音乐和动态图像信息(节目视频、短视频、电影、微电影等等)的主要传输工具。在技术上为了避免未经许可的下载、复制并节省使用装置的空间和资源运用,反而刻意不将其内容予以固定到任何载体之上(否则可能需要占用大量的储存空间,更长的等待时间,在相当程度上自然会冲击到整体的观赏体验)。[7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79]
对于实时直播的任何节目而言(包括体育赛事),既然是“即时性”的直播,自然就意味著“时间”是其主要的经济价值所在,而且永远有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纯粹从技术而言,每一个透过网络传输的压缩信息包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有形载体,在概念上与传统的类比式(analogue)或有限数字(digital)电视讯号透过有线、无限或卫星的传输并无如何本质上的不同,而其最终呈现与以往透过计算机的随机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 RAM)的暂时性复制(transitory duplication)也相当的类似。
这就意味著至少在传输和呈现的两个环节上都已经产生了“固定”,否则视频画面便根本无法呈现。因此,鉴于赛事的直播本身就是个动态性的过程,只要符合“独(原)创性”的要求,恐怕实在没有理由基于在某个特定的或静态的技术节点上以还未“固定”为由去否定获得著作权的可能。
此外,既然将赛事的内容拍摄为单张的照片传输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如果按照二审的判决连续的摄像画面组合却无法获得著作权显然已是相当的不可思议。尤有甚者,只要赛事还未结束,就无论如何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此时如果有人以任何链接、讯号劫持的方式撷取视频转播也不可能构成著作侵权行为了。这显然不是著作权的立法体系所希望见到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否应该赋予著作权(而非仅邻接权)的保护,其中关键还是在于是否有“独(原)创性”。至于究竟要有什么样的“创作高度”是根本不需要去探究的,也恐怕穷法院之力永远也无法厘清;至于具体归类为什么形式的作品并非那般重要,毕竟不同类型的作品之间原本就可以竞合,从来不相互排斥,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本来就会经常产生方枘圆凿的问题。
四、涉及再转播的侵权责任应予厘清
视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形,第三人对体育赛事、电子游戏团体竞技的直播从事未经许可的再转播可能要负直接侵权责任,也可能涉及间接侵权责任,并潜在的涉及到对数种权利的侵害。但在现行法的规制下却也有可能得以完全规避其责任,关键是再转播的主体为谁以及具体的转播是否为交互(互动)方式。但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因为立法上的缺失所导致。
交互(互动)式的传播是指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透过网络的再转播,其对节目讯号的传播可能属于交互式也可能不是(传统的转播为非交互(非互动)式,而点播则显然属于交互(互动)式);从事再转播的主体可能是电视台也可能是任何的网站。[80]依据现行法的规定,只有电视台从事未经许可的交互式再转播才可能会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如果是属于“非交互(互动)式”的网络传播(或“网络定时传播”)或从事再转播的地方在技术上不构成“电视台”时,该第三人就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这个人为规制上的疏漏自然让潜在的侵权者有机可趁,也只能透过立法修改来弥补。
根本的解决之道,首先是必需修改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建议不妨就直接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第八条“向公众传播权”的规定,也可与既有的国际规则与要求完全无缝接轨。[81]另外应对《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电视台”提供更为明确的定义。
重点应该是让权利的保护范围涵盖到所有在网络上的交互(互动)式(向公众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s to the public)与非交互(互动)式的传播(向公众提供权right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其中关键是提供接触或取用(access),至于潜在的公众是否确实接收到则在所不问,也完全符合所谓“三网融合”的发展现状(亦即电信网、有线电视网以及互联网(包括行动装置)的相关业务融合,并非物理上的整合),不需要去纠结于何种特定的播放或传播形式。[82]
其次,依现行《著作权法》,广播电视组织所享有的是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规定的“广播权”,但很遗憾未能涵盖有线广播。[83]《送审稿》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拟议的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借鉴、配合了《保护广播电视组织条约》的研拟方向先将“广播权”的名称改成了“播放权”(包括以无线或有线的方式公开播放或转播作品或是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再搭配表演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就应可覆盖到除了点播之外的所有广播行为,从而可以弥补现行法对这个问题的疏漏之处。
五、《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宜扩张适用
无论从国际公约的保护框架来看或是从制度的目的和政策的视角而言,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相互排斥或是谁挤占了谁的位置的“关系”问题,而是后者(或后者的一部分内容)对前者如何给予补充的问题,亦即彼此并不具有替代(或取代)的关系,但却可互补。[84]
因此《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便规定:“……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行为或做法亦应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至于“诚实的习惯做法”的具体含意为何则还需由有关国家的司法当局来解释,但于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一概念不应局限于发生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的诚实习惯做法,还应顾及国际贸易中所确立的相应概念。[85]
虽然如此,各个得以适用的法规毕竟有其本身特定的要件与范围,一旦产生构成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侵权(事实上或潜在的)竞合问题时,仍应先行辨别各自的内涵与分际,以免造成不当混同,让本不相关的因素却相互牵扯纠结到了一起,反而对原本应有的认定造成混乱。例如,在分析、审度是否构成对著作权的侵权问题时,就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对消费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不需要探求是否对消费者有构成混淆的可能(那是在认定有无商标侵权时才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就显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提供补充保护有一定的限度。目前国内的通说也是采取类似的观点。例如: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专门法共同组成。知识产权专门法是财产法,它通过赋予权利人某种专有权,提供一种对世性的积极权利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行为法,它不是提供对世性的积极权利保护,而是一种消极性保护,即禁止以违反工商业道德或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侵犯他人的利益。由于两者的保护角度和保护条件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专门法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专门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专门法发挥补充作用的有限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专门法的补充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条件和门槛,并非无限地兜底适用。”[86]
更具体的说,“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保护作用的发挥不得抵触知识产权专门法的立法政策,凡是知识产权专门法已作穷尽性规定的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上不再提供附加保护,允许自由利用和自由竞争,但在与知识产权专门法的立法政策相兼容的范围内,仍可以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给予保护。”[87]
在第三人透过网络把一场体育或网络游戏的赛事直播从事未经许可的再转播的情形,其中至少牵涉到了著作侵权的问题,也涉及了对权利人的商业模式与运营从事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对于后者,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所订出的指导原则,法院应聚焦于各个与著作权的侵权认定无关或以外的其他因素,检视它们是否完全符合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明确规定的某种或多种(商业)侵权行为要件。
现行《著作权法》立法上的瑕疵与不足导致权利人无法从特定类型的案件获得适当有效的救济,于是只能另辟蹊径,把本来只是做为辅助或附带诉求性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变成了主张侵权的主要依据,也就是把辅助变成了替代。
但即使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实在难以找出可以准确适用的具体条款。于是只好同许多其他过去的案件一般,把原本只是做为一般宣示性质的第二条第一款(诚信原则与商业道德条款)“异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可以让法院完全自由裁量并扩张适用的“霸王条款”,也无异于形成了对适用特别法(著作权)的特别替代与延伸(反不正当竞争)的再特别扩张(霸王条款)。[88]这种“特别+特别+再特别”的做法完全是一时性的“权宜之计”,虽然多少是出于无奈,但却终究对法律的适用与解释造成了很大的扭曲,长此以往恐怕将对未来的法学发展与法制建设产生不利的后果。
伍、结论
著作权所要保护的,是具有“独(原)创性”的表达。设定这个要件是要在制度上求取一个相对适当的平衡:作者所汲取的来源或素材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特定的作品是否经过某种转化再由作者自行表达或呈现,从而不是复制品或抄袭之作。换句话说,可受著作权保护的转化是指作者透过自行的筛选与安排来呈现对其作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指作品的表达方式或呈现至少包含了一些最起码的个别创意。
欧盟法院在《足球联盟赛程表》案的判决后,已然确立了欧盟对于“独(原)创性”的标准与美国已经相当的接近,只要特定作品是由作者所独力自为的创作,而且同时具有某种最低程度的创意便已足够。至于以往对于“创作高度”的要求或是只要有“智力劳动成果”就可以获得权利的论述其实都是悖论与误区,会导致发生让原本根本就不应受到保护的事物却都可以获得著作权,产生很大的混乱。
固然不同法系的国家在表面上所使用的文句或许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因为承认人格(身)权,所以著重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个性”);英美(普通)法系则是著眼于特定作品与先前其他作品的比较(作品的“创造性”),但详细检视便不难发现这两者无非是一体的两面,必需相互为用。
“横看成岭侧成峰”,两大法系的论述其实并无如何实质上的不同,至于特定作品的美学价值、创作目的或是社会反应如何皆与是否符合著作权保护的认定完全无关。同理,从立法政策上对于不同的作品要求必需具备不同的创作高度才能获得著作权,甚至据此给予程度不同的权利保护,不但与著作权的本质相悖,更注定会制造出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在实践上只会让当事人与法院都无所适从。
在另一方面,“邻接权”(或“相关权”)是相对于作者对其文艺作品著作权之外的、范围相对也相当有限的独立排他权利。其所保护的客体并非作品的本身,而是对特定作品(例如电视节目或录音录像制品,无论该作品是否受到或仍受著作权保护)的表演(有别于著作权人的表演权,后者包括对节目讯号的传播等)、广播或首次录制(或发行)等三种类型,其所保护的主体则是表演者、制作人或广播组织,别无其他。因此在实践上对邻接权的范围与解释不宜任意扩张。
在具体的实践上,视个别案件的案情,第三人对体育赛事、电子游戏团体竞技的直播从事未经许可的再转播可能要负直接侵权责任,也可能涉及间接侵权责任,并潜在的涉及到对数种权利的侵害。但在现行法的规制下却也有可能得以完全规避其责任,关键是再转播的主体为谁以及具体的转播是否为交互方式。但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因为立法上的缺失所导致。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必需修改现行《著作权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并且必需符合国际公约与协定的要求,与国际完全接轨。最直截了当也是风险最小的做法就是直接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八条“向公众传播权”的规定,也可与既有的国际规则与要求完全无缝接轨。另外应对《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电视台”也必需提供更为明确的定义,这样即可让权利的保护范围涵盖到所有在网络上的交互(互动)式(向公众传播权)与非交互式的传播。
目前正逢《著作权法》进行大规模修改的关键时刻。最近出现的案件与探索正好让著作权保护体系的一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再次浮上了台面,也呈现出了一些既有规制与立法修改草案的不足之处。由于这些案件的背后通常都蕴含著庞大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相关的法规要如何修改注定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注定会有一定的争论性。谨诚挚地盼望各界能对其中各项环环相扣的问题以温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反覆辩证,把这个需要细致平衡的钢索能够妥善走稳。
注*作者孙远钊教授,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并于北京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作者特别感谢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前副司长许超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武幼章两位先生在百忙中拨冗指正,让作者得以修改文稿中的错误疏漏之处。惟本文文责概由作者自负,不代表作者服务单位与点评者的立场。
[1]“大哉问”是“问的真好”之意,出自《论语》〈八佾〉第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译文:林放询问孔子,婚丧喜庆举行的准则是什么。孔子说:“问的真好啊!喜宴的举办,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礼的举办,与其简易,不如安静哀戚。”
[2]《送审稿》第三条第一款:“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成果。”与现行法规的最大区别是扬弃了不符国际规制的“有形形式复制”要件而加入了“以某种形式固定”的要求。
[3]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Organization (WIPO), Guide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Paris Act, 1971), 2.4-2.6,at 13.
[4] Adolf Dietz, The Concept ofAuthor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155 RevueInternationale Du Droit D'auteur (R.I.D.A.) 2, 10-12 (1993). 例如,美国版权局特别在其最新(第三)版的《美国版权局实践指南》中表明了此点,并针对猿猴自拍照所产生的问题例示不受著作权的保护。参见U.S.Copyright Office, Compendium of the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3rdEd.), § 313.2 (2014); Burrow-Giles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 58 (1884)。然而关于这个由一个几内亚的黑冠猴(Crested Macaque)拿了摄影师大卫斯雷特(David Slater)的器材所拍出的一系列“自拍照”(selfies)是否具有任何的著作权的问题并未就此停歇。美国的“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 PETA)已经出面代表该自拍的黑冠猴(并替其取名为“纳汝投”Naruto)起诉,试图改变既有的司法判例。但联邦地区法院北加州分院并未接受,判决原告方并不具有任何的著作权。参见Naruto v. Slater, Case No. 3:15-cv-04324 (N.D. Cal. 2016)。本案原告目前已将全案上诉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候审。
[5] SamRicketson,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1886-1986 (1987), at 232.
[6]例如,英国的《1988年著作权、设计暨专利法》(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第一条、加拿大《著作权法》(Copyright Act)第四条第一款、澳大利亚《1991年著作权修改法》(1991Copyright Amendment Act)第三十二条以及美国《1976年著作权法》(Copyright Act of 1976)第一百零二条等规定。
[7] Baker v. Selden, 101 U.S.99, 102 (1879)(“The copyright of the book, if not pirated from other works,would be valid without regard to the novelty, or want of novelty, of itssubject matter”).
[8] “额头流汗”或“汗流满面”源自《圣经》(创世纪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you will eat your food until you return to theground, since from it you were taken; for dust you are and to dust you willreturn.)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22年的一个判决将此一概念转化适用到了著作权。参见Jeweler’s CircularPublishing Co. v. Keystone Publishing Co., 281 F. 83, 88 (2d Cir. 1922)。
[9]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499 U.S.340 (1991).
[10] Id. at 345.
[11] Legge 22 Aprile 1941, N. 633 – Protezione del Diritto D’autore e diAltri Diritti Connessi al suo Esercizio (2010).
[12] Bedienungsanweisung (“OperatingInstructions”), Case No. I ZR 147/89, Bundesgerichtshof (German Federal SupremeCourt)(October 10, 1991), 23 I.I.C. 846 (1992); Leitstze (“Headnotes”), Case No. I ZR 190/89, Bundesgerichtshof (November 21,1991), 24 I.I.C. 668 (1993).
[13] P. Bernt Hugenholtz, Dutch CopyrightLaw, 1990-1995, 169 R.I.D.A. 129, 135 (1996).
[14] Code de la propriétéintellectuelle (version consolidée au 17 mars 2017), Article L111-1:“L'auteurd'une oeuvre de l'esprit jouit sur cette oeuvre, du seul fait de sa création,d'un droit de propriété incorporelle exclusif et opposable à tous.” 本条文的中文内容参酌了黄晖博士的翻译文本。
[15]Jane C.Ginsburg, French Copyright Law: AComparative Overview, 36 J. CopyrightSociety 269, 274 (1989).
[16]参见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其原文为:“著作物 思想又は感情を創作的に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つて、文芸、学術、美術又は音楽の範囲に属するものをいう。”(昭和45(1970)年5月6日法律第48号修订)。
[17] Case C-604/10, FootballDataco Ltd. and Others v. Yahoo! UK Ltd. and Others, Judgment of the Court(Third Chamber), 1 March 2012.
[18]任自力,曹文泽,《著作权法:原理规则案例》(1991),第5页。
[19] WIPO, Guide to the Berne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Paris Act, 1971)(1978),at 13 (“[The work] may be produced for purely educational purposes or with amerely utilitarian or commercial aim,without this making any difference to the protection it enjoys”).
[20]因此,美国著作权法学者Jessica Litman教授便曾表示:“由于作者们必需是从其他人的先前作品从事必要的重塑,一种认为作者的原(独)创性是源自从无到有的观点— 以及作者乃是从其心灵最深处的创造予以加总呈现— 不但有缺陷而且是误导。”换句话说,所有的创作都不外是对既有作品的某种“重组”(recombination)与“转化”(transformation)。参见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L.J. 965 (1990)(其原文为:“Becauseauthors necessarily reshape the prior works of others, a vision of authorshipas original creation from nothing – and of authors as casting up truly newcreations from their innermost being – is both flawed and misleading”).
[21] Act of March 3, 1891, 26 Stat. 828, s. 517, § 6.
[22] Bleistein v. DonaldsonLithographing Co., 188 U.S. 239 (1903).
[23] Id., at 251. (“It wouldbe a dangerous undertaking for persons trained only in the law to constitutethemselves final judges of the worth of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utside of thenarrowest and most obvious limits.”)
[24] 17 U.S.C. § 101 (2016)(definition of applied arts and industrial designs).
[25]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Ltd. v. 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Ltd., [1916] 2Ch 601; Ladbroke (Football) v. William Hill(Football) [1964] 1 WLR 273; IndependentTelevision Publications Ltd. v. Time Out Ltd. [1984] FSR 64.
[26] Case C-5/08, Infopaq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2009] ECDR 16.
[27] Inkasso-Programm(“Collection Program”), Case No. I ZR 52/83, Bundesgerichtshof (May 9, 1985),17 I.I.C. 681 (1986); Van Dale v. Romme,Hoge Raad, January 4, 1991.
[28] Jacques Barzun, The Paradoxesof Creativity, 58 American Scholar337, 351 (1989)(“It has not only diluted the meaning of creative; it has alsoglutted the market with innumerable objects and performances arbitrarily calledart, thereby making it even more arduous for true creation to find a public.”).
[29] Supra note 8, 111 U.S.358. 另参见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2014),第73页。
[30] 17 U.S.C. § 410(c)(2016).
[31]凌宗亮,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类型化及其路径—兼谈《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14条的修改,《法治研究》,第105卷第3期,第27-35页(2016年5月),转载于《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52157。
[32] WIPO, Broadcasting &Media Rights in Sport, http://www.wipo.int/ip-sport/en/broadcasting.html.
[33]依据《罗马公约》和WPPT,“邻接权”(或“相关权”)是相对于作者对其文艺作品著作权之外的独立权利,而且其所保护的客体并非作品,而是对特定作品(节目或录音制品)的表演(有别于著作权人的表演权)、广播或首次录制(或发行)等三种类型,其所保护的主体则是表演者、制作人或广播组织。至于“邻接权”(或“相关权”)的具体内涵为何,是否必需具有“独(原)创性”,则依其成员国的国内立法来定义。这是因为各国对此一问题的处理仍有分歧。参见WIPO, Guide to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reaties Administered byWIPO and Glossary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2003), at 133。如欧盟便规定了第四种类型:制作人对其影片的首次固定权(right of first fixation)。Directive 2001/29/EC on the harmonization of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t.2(d), [2001] O.J. L 167, at 10。目前国内的通说是对于不具“独(原)创性”但仍具有某些价值的非物质劳动成果纳入到“邻接权”的保护范畴,也称为“广义”的著作权保护。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三版,2011),第183页。
[34]Statement ofPolicy; Registration of Compilations, 77 Fed. Reg. 37,605(June 22, 2012).
[35] AaronN. Wise andBruce S. Meyer,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and Business,vol. 3 (1997), at 1714. 不过国内学者对此有不一致的论述,无法确定所指称的是否即为“在地权”。参见袁博,体育比赛直播法律关系及维权路径探析,《中国版权》,2017年第3期,第37-41页(“在西方,这一权利被称为‘场地准入权’,即许可比赛直播者进入其控制的比赛场地直播比赛实况的专有权利”);凌宗亮,前注31(“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不符合版权保护条件的体育赛事应当如何进行保护,国内外理论研究提出了众多理论和观点。西方国家经历了‘赛场准入说’ 、‘娱乐服务提供说’到‘企业权利说’的发展历程。赛场准入说认为,赛事转播权源于已经获得法律承认的另一项财产权利,即体育场馆所有人对体育场馆的所有权或管理人的占有权……”)。
[36]王迁,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兼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82页;王迁,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法学家》,2014年第5期,第125-136页;另参照张伟君,关于网络转播广播作品与王迁教授商榷,《知产库》,2017年7月13日,http://www.weidu8.net/wx/1013149993596091。
[37] Joined Cases C-403/08 andC-429/08,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 and others v. QC Leisure andothers and Murphy v. Media ProtectionServices Ltd., [2011] ECR I-9083.
[38] Asser Institute, Study onSports Organisers’ Righ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2014), at 19.
[39]同前注37 (“[S]porting events, as such, have a unique and, to that extent,original character which can transform them into subject matter that is worthyof protection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of works, and that protection can begranted, where appropriate, by the various domestic legal orders.”)。
[40] NBA v. Motorola, Inc.,105 F.3d 841 (2d Cir. 1997); seealso Thomas Margoni, The Protectionof Sports Events in the EU: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fair Competitionand Special Forms of Protection, 47 IIC– Int’l Rev.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386 (2016).
[41]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Associated Press, 248 U.S. 215 (1918).
[42]同前注32。另参见前注37。
[43] Directive 2006/115/EC on rental right and lending right and on certain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t. 3.1(d), [2006] O.J. L 376, at 28 (hereinafter Rental Directive).
[44] EU Rental Directive (Arts. 7–9), Satellite Directive, and theInfoSoc Directive (Directive 2001/29/EC, Arts. 2(e) and 3(2)). See alsoTRIPs Agreement, Article 14(3); Rome Convention, Article 13. See also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Distribution of Programme-Carrying Signals Transmitted by Satellite, done atBrussels on May 21, 1974.
[45]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Ltd v. TVCatchup Ltd. of 7 March 2013, 25.
[46]如果依照传统的法理逻辑,邻接权的存在是以著作权的存在为依归或是做为前提。因此现在改称为“相关权”,正是可以避开传统名义所意涵的的局限性。
[47] Case C-279/13, C MoreEntertainment AB v Linus Sandberg of 26 March 2015; Hgsta domstolen, Ml B3510-11, 29/12/2015 (Supreme Court in Stockholm, Ml B 3510-11, 29 December2015).
[48] Directive 2001/29/EC, Article 3(2), supra note 32.
[49]同前注47。
[50]同上注。
[51] Henrik Wistarn and Annie Kabala, No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Sport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 Newsletter,October 3, 2016, at http://www.internationallawoffice.com/Newsletters/Intellectual-Property/Sweden/Advokatfirman-Lindahl/No-copyright-protection-for-sport-broadcasts.
[52] H.R. Report No.94-1476(1976), at 52-53.
[53] Baltimore Orioles, Inc. v.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 805 F.2d 663 (7thCir. 1986), cert. denied, 480 U.S.941 (1987).
[54] National BasketballAssociation v. Motorola, Inc., 105 F.3d 841 (2d Cir. 1997).
[55] Melville B. Nimmer &David Nimmer, 1 Nimmer onCopyright §2.09[F] (1996), at 2-170.1.纵使假定体育赛事的本身是某种“作品”,从而可以享有著作权,实际上这就意味著对于一场赛事有所贡献的两个球队、所有的球员、教练、经理、裁判、球场工作人员、媒体人员乃至于所有的球迷等等都是“共同作者”,而这也形同相互抵销,让“权利”的运用完全不可能。
[56] Product Contractors, Inc. v.WGN Continental Broad. Co., 622 F. Supp. 1500 (N.D. Ill. 1985).
[57] Michael J. Mellis, InternetPiracy of Live Sports Telecasts, 18 MarquetteSps. L. Rev. 259 (2008).
[58]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v.PrimeTime 24 Joint Venture, 211 F.3d 10 (2nd Cir. 2000).
[59] Metro-Golden-Mayer Studios,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
[60] Copyright Office’s Views onMusic Licensing Reform: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urts, theInterne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S. House ofRepresentatives, 109th Cong., 1st Sess. (June 21, 2005)(Statementof Marybeth Peters, then Register of Copyrights).
[61] Fortnightly Corporation v.United Artists Television, Inc., 392 U.S. 390 (1968); Teleprompter Corporation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415U.S. 394 (1974).
[62]同前注52,第86-87页。这三个条文分别是第一○一条对于“表演”与“公开”的定义(即所谓的“传输条款”)以及第一一一条关于节目讯号再传播的强制(法定)许可规定。
[63]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Inc. v. Aereo, Inc., 573 U.S. __, 134 S.Ct. 2498 (2014).
[64]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小白龙动漫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提出了如下的的论述:“作品的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并表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思想。独创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加以判断的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实际上,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其独创性要求体现作者在美学领域的独特创造力和观念。因此,对于那些既有欣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客体而言,其是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取决于作者在美学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所体现的独特个性和创造力,那些不属于美学领域的智力劳动则与独创性无关。”其中的第一句和第二句是完全正确的,但除非法律另有明文、特别的规定,之后的论述就恐怕还需要再做斟酌。譬如一位小朋友(或任何人)的信笔涂鸦纵使对多数人而言毫无艺术或欣赏价值,但也绝不应妨碍该当事人取得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根本不应有这种歧视性的对待。参见(2013)民申字第1358号民事裁定。
[65]《著作权法》第一条。
[66]同前注33。
[67]邹韧,最佳的法律路径在哪儿(网络版标题:巨资购买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该如何保护?司法界和学术界各有说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7月6日,第五版(《版权监管周刊》)。
[68]著作权法《送审稿》第五条第一款拟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表达。”另在同条第二款第十二项拟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并且能够借助技术设备被感知的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以及类似制作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这就可以明确涵盖关于体育赛事的转播。但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就意味著在直播的情形,必需是录像录音与讯号的传输是同步进行或先录后传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如果是先传后录就无著作权可言。
[69]该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70]武幼章,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否构成作品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新浪网:在线推的博客》,2018年3月31日,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99ad30102xmhd.html。
[7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2018年3月30日。
[72]另参见《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2015)京知民终字第1055号,2018年3月30日。
[73]前者是基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款对“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定义,而后者则是法院试图从“不同邻接权客体之间的共性”以及“与著作权区别”等“体系化分析”推导出“将一系列连续画面同时规定为电影作品与录像作品……,二者的差别仅可能在于独创性程度的高低,而非独创性的有无”。同前注71,第25-27页(黑粗体为判决书所加)。
[74]参见前注3,第13页。
[75]其原文为:“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rks ‘produced by a processanalogous to cinematograph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a special provision to theeffect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 works expressed by a processproducing visual effects analogous to those of cinematography.” 参见WIPO, Record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Conference of Stockholm: June 11 to July 14, 1967 (1971), vol. 1, at 80 (Documents S/1,at 10 and S/190, at 173); Report on the Work of Main Committee I(Substantive Provisions of Berne Convention: Article 1 to 20), vol. 2, at1131。
and which are fixed on some material support would be considered tobe cinematographic works.”
[76]参见前注3,第15页(“In the end, after it was decided to leave thewhole question of fixation to national laws (paragraph (2) of Article 2), the [Berne]Convention was able to … provid[e] that it was simply a matter of ‘worksexpressed by a process analogous to cinematography’. It is not so much theprocess employed which is analogous as the effects, sound and visual, of such process.”)。
[77]同上注。
[78]所谓的“流媒体”或“流式媒体”技术就是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置于网站服务器,再由视频服务器向用户计算机顺序或实时地传送各个压缩包,让用户一边下载一边观看、收听,而不要等整个压缩文件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上才可以观看的网络传输技术。
[79]法释〔2006〕11号,2006年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06次会议通过,自2006年12月8日起施行。
[80]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Related Rights)正拟议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电视组织条约》(WIPO Treaty to Protect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其中对于“广播”的定义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其中的差异在是否要另外独立定义一个“有线广播”。无论如何,在计算机网络上从事的播送不构成“广播”。草案也加入了对于“转播”、“近同时播送”、“延时播送”等名称的定义,试图把包括网络传播(webcast)等在内的各种行为都能全面覆盖。参见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vised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and Other Issues, SCCR/34/3 Corr., 34th Session, March 13, 2017,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42296&la=EN。
[81]第八条:“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第(1)款第(ii)目、第十一条之二第(1)款第(i)和(ii)目、第十一条之三第(1)款第(ii)目、第十四条第(1)款第(ii)目和第十四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关于本条规定的《议定声明》(列于注七)则进一步表示:“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并且,第八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阻止缔约方适用第十一条之二第(2)款。”
[82]张伟君,前注36。张教授建议把相关的法条文句修改为:“向公众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广播权以外的任何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包括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笔者对此完全赞同。
[83]这个条文原本是引进《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
[84]参见《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二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1997);另参见郑成思,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网络版载于《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4017。
[85]《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1997)关于第一条的注释,§1.02。
[86]准确把握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情况通报》第5期,2012年2月28日,载于http://zscq.court.gov.cn/sfzc/201304/t20130426_183682.html。
[8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18号(2011年12月16日印发)。
[88]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即“中超赛事转播案”),(2014)朝民(知)初字第40334号民事判决(2015年6月3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于2018年3月30日出台了对本案的上诉(二审)判决,参见前注71,但关于不正当竞争的部分并未上诉)。另一个迂回途径是扩张解释《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广播组织权”当中的“转播权”范围。不过这么做依然会面临到适用主体的困境,即从事网络转播的网站等是否当然构成“电视台”或“广播电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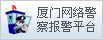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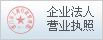




 在线客服1号
在线客服1号 扫一扫微信咨询
扫一扫微信咨询